2024-10-17 09:44:45|网友 |来源:互联网整理
1、岁寒三友
2、三纲五常
3、韦编三绝
4、三足鼎立
5、三马同槽
6、三途判
7、三先天
8、三教顶峰
9、灭度三宗
10、无定三绝
11、三只快乐的小猪
12、三人群
13、三人众
14、三只单身汪
15、三个快乐的男生
16、三只小黄鸭
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和王家卫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繁花》,给人印象迥异,但都有特色,也有深度,让我联想到恩格斯的一段著名论述。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先引用了黑格尔的一段话:“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
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
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种种现象,同样可以说是“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
发展民营经济、引进股市、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摸着石头过河等等政策措施,都可作如是观。
放到《繁花》中具体人物的身上,如阿宝,最初或许只是因为初恋的雪芝远嫁了香港的有钱人;如玲子,或许只是因为不甘于在东京会所里做一辈子的服务员;如范总,或许只是想到上海南京路来发财;如汪小姐和魏总,或许只是想到和平饭店的顶层俯瞰上海的繁华;如李李,或许只是要为她逝去的恋人还债……繁花红尘,芸芸众生,这其中掺杂着或明或暗的情欲贪欲,飘茵落溷的悲欢离合。
个人机缘的凑巧与不凑巧,岁月阴错阳差的撞击,命运的戏剧性与不可测性。
但这些人毕竟都抓住了历史的机遇,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投入了自己,演出了各自精彩的一幕。
他们的动机和行为在传统意义的框架中都说不上怎么高尚,身上也或多或少带有反英雄色彩。
不过,我们对改革开放之初的这段历史,绝对不能用今天流行的一些陈词滥调来生搬硬套。
《繁花》里的这些人物,一个个用生动鲜明的形象,深刻阐述了这段历史。
王家卫导演说过,小说与电视剧是两回事,所以他请读者也要去看小说《繁花》。
小说里有两个重要的人物,小毛与沪生,在电视剧中并没有出现。
电视剧是再创作,有自己的选择、增删,这无可厚非。
这里先提一下我怎样开始对这两个人物细读、思考。
多年前,金庸先生及其夫人特意安排,请我在香港香格里拉酒店一起吃饭,我是金庸先生的超级粉丝,自然受宠若惊。
席间,我给先生带去了为他写的文章,还讨论了怎样用通俗文学的形式呈现严肃、形而上的思想。
金庸先生去世时,深感欠情良多,在《南方周末》上写了一篇悼念文章。
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今年年初我在上海与金宇澄有一次长谈,谈他的《繁花》,也又一次谈到了金庸的《天龙八部》。
我说到,《繁花》中三位结义兄弟分手的场景,与《天龙八部》中三位结义兄弟在少林寺前联手对敌的场景,有异曲同工之处,而金宇澄告诉我,王家卫也特别喜欢《繁花》中三位结义兄弟分手的一段。
我在《南方周末》这篇文章中探讨了在香格里拉酒店中曾想对金庸先生说的,却未能仔细分析的那一场景。
萧峰、虚竹、段誉这三个结拜兄弟怎样在少林寺前舍身忘死抗敌。
萧峰自是大侠,虚竹却一心向佛,段誉更是平日里只顾得上王姑娘的情种。
偏偏就在那一刻,“段誉不由得激起了侠义之心,大声道:‘大哥,做兄弟的和你结义之时,说甚么来?咱们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今日大哥有难,兄弟焉能苟且偷生?’”正是武侠话语体系中的江湖义气,在片刻间让他忘掉一切顾忌,甚至顾不上王姑娘就在人群之中,像换了个人似的直冲着慕容复杀了上去……“(虚竹)见段誉顾念结义之情,甘与共死,当日自己在缥缈峰上与段誉结拜之时,曾将萧峰也结拜在内,大丈夫一言既出,生死不渝,想起与段誉大醉灵鹫宫的豪情胜慨,登时将甚么安危生死、清规戒律,一概置之脑后……胸中热血如沸,哪管他甚么佛家的五戒六戒、七戒八戒,提起皮袋便即喝了一口……”,也一起杀了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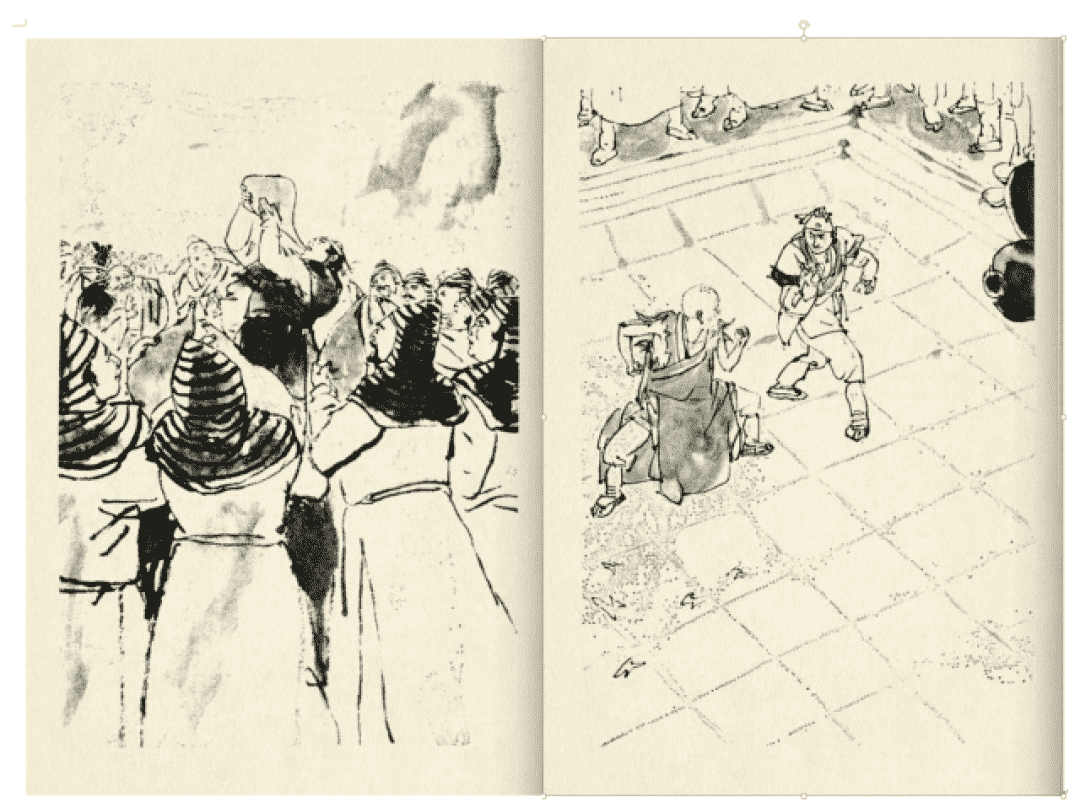
《天龙八部》插图。
只是关于小说《繁花》,在纪念金先生的文章里未便展开,恰适电视剧播出之际,在这里补上几笔。
小毛、阿宝、沪生也是所谓的结拜兄弟,平日关系甚好。
不过,小毛碰到了一个问题。
小毛早先与银凤有染,但小毛娘与他两个师傅都十分坚持,要他明媒正娶另一个女人春香。
那天,他正巧听到阿宝、沪生与银凤间的一段对话。
小毛靠了门框,一股热血涌上来,慢慢走近理发店。
三个人发现小毛,身体一动。
银凤穿一件月白棉毛衫,手拿一条毛巾,路灯光照过来,浑身圆润,是象牙色。
但此刻,小毛毫不动心,也并不难过。
小毛拿出春香的照片说,讲的不错,我确实要结婚了,从现在起,大家不要再虚伪,不需要再联系。
沪生说,小毛,作啥。
小毛说,本来就不是结拜弟兄,我走我独木桥,以后不必要来往了。
阿宝说,小毛,酒吃多了。
小毛说,我死我活,我自家事体,从今以后,大家拗断。
阿宝与沪生立起来说,小毛。
银凤不动,凛若冰霜,突然蹲下来抽泣。
小毛说,对不起,大家到此为止,我决定了,说一不两。
说完这句,小毛十分平静,突然感到无所畏惧,能独立面对一切磨难,小毛一步一步走到楼上,关门睏觉。
小毛与结拜兄弟阿宝、沪生以及银凤的决裂来得十分突兀,出乎所有在场者的意料,也包括小毛本人。
当年我为金庸先生带去的“金庸武侠小说三人谈”一文中,我曾运用了西方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一个观点来阐述金先生的小说。
在新历史主义中,人们其实生活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有官方的、主流的、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也有非官方的、非主流的、非传统的、在边缘状态的。
正是在这些不同的话语体系中,人们的所作所为获得了认可与否定。
错还是对,做或不该做,有还是没有任何价值意义。
人们也因此决定了(可以说被决定了)自己的行为。
用福柯的话来说,甚至人的主体,同样是在这些话语体系中得到了建构或解构。
不过,这些话语体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存在并不是单一或静态的。
相反,它们可能是在不断的对抗、谈判或妥协中。
在一般的情况下,某一特定的话语体系会占有统治地位,但在不同的情境中,另一话语体系也可能突然占了上风,颠覆了局面,甚至颠覆了一个人所想当然的主体性。
在小说《繁花》中,小毛因此就这样突变了。
在此之前,他的生活方式与话语体系,跟阿宝、沪生以及银凤一样,多少有离经叛道的意味,但在那一刻,他却倒向了传统的主流话语体系,成家立业,太太平平过日子。
有意思的是,金宇澄在这里还特意安排了小毛的母亲与两个师傅给他做这方面思想工作。
《天龙八部》中虚竹、段誉的突变,也不妨说江湖义气的话语体系在这一刻彻底压倒了其他话语体系。
关于这种突变,我们会说是鬼迷心窍,或福至心灵,讲的是同样意思,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而已。
不管怎么说,这些现代或后现代的理论观点往往写得抽象、枯燥、艰涩,几乎令人难以卒读,可在《天龙八部》与《繁花》中,这一切却跃然纸上,生动、深刻、令人不得不信服,击节赞叹。
毕竟,小说家不是要去写思想或哲理,却是要在叙事中自然地——甚至是潜意识地——展现形而上的层面,让读者去思考,去得出自己的结论。
把小毛这三个结拜兄弟与萧峰这三个结拜兄弟的场面写得如此跌宕起伏,慷慨激昂,同时又在此之上呈现一个形而上的层面,写出了人们在囿于话语体系中身不由己的挣扎。
这在西方后现代理论中,也可以说是话语在说人,而不是人在说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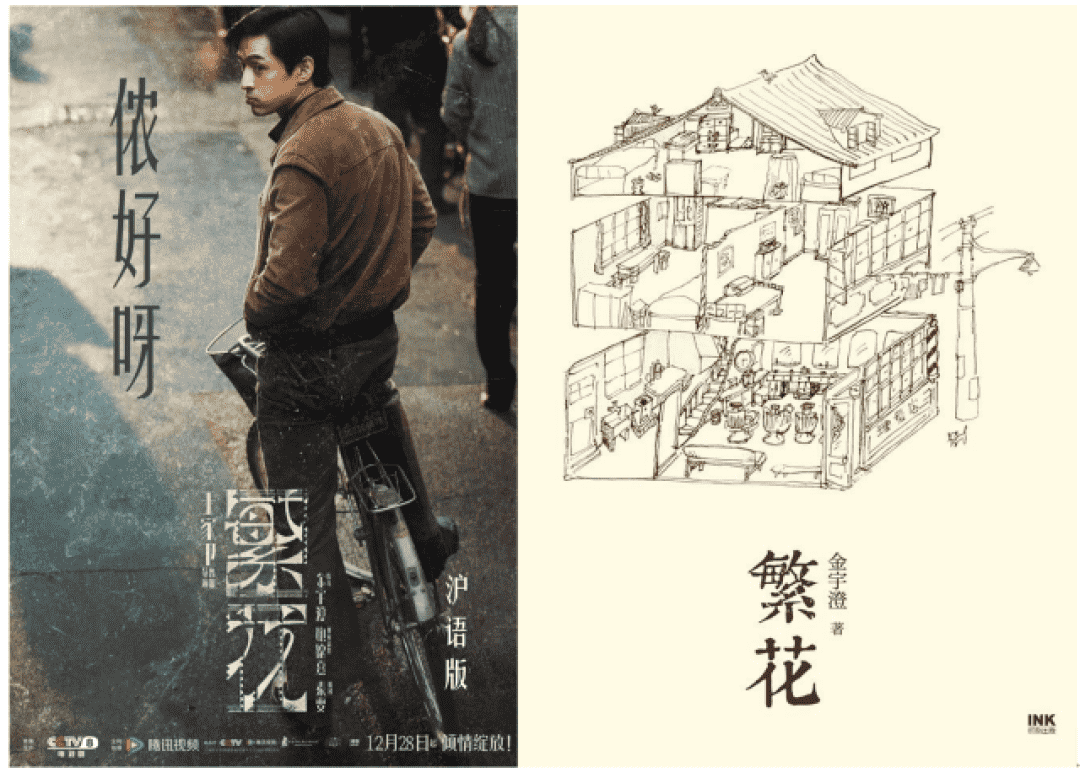
小说《繁花》与电视剧《繁花》。
谈小说《繁花》与电视剧《繁花》,必定要涉及不同的形式结构。
小说《繁花》的叙事是片断性或碎片性的,读起来颇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空间形式感。
这是美国批评家约瑟夫·法兰克(Joseph Frank)提出的一个著名理论。
他认为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大多背离了莱辛(Lessing)所说的对时间叙事形式的依赖,却更趋向于类似现代造型艺术的空间。
如艾略特的《荒原》碎片化处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彻底抛弃传统的线性叙事形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大量的细节叠加。
法兰克提到了《荒原》,说人们在讨论《荒原》时,总会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这首划时代长诗的形式,却无人能否定《荒原》有其独特的形式。
在他看来,一旦放入空间形式中加以观照,《荒原》就不是那么杂乱无章了,草蛇灰线,隐隐可现。
无庸赘言,电视剧得有不同的形式、节奏、悬念。
必须要能让广大观众在电视机前,从头到底,一集一集看下去。
每一集都要承上启下,还要有自己的悬念,观众看得投入、津津有味。
在电视剧中,线性叙事形式,就不可避免了。
说到底,电视剧的观众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读者的美学需求是不一样的。
我太太也是每天拉着我一起看,看完了还要一起讨论。
我这篇文章中谈到的一些问题,或多或少是这样讨论出来的。
我喜欢小说《繁花》,还有个后来才慢慢悟出的原因。
《繁花》让我联想到自己写《红英之死》的过程。
我当时在一个学校教书,有办公室时间,没学生来,反正空着也是空着,便随心所欲地写了起来。
起初甚至都未想过要写推理小说,也不知道以后是否能出版。
于是,兴之所致,随笔写去,压根儿没去考虑推理小说的一些结构俗套。
结果反而是无心插柳,无为而无不为。
《红英之死》出版二十多年后,去年还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全球最佳(不同语言、不同时代)一百本推理小说之一。
我想“道可道,非常道”,或许是原因之一。
金宇澄的小说《繁花》,最初不是发在他主编的《上海文学》,而是在一个小众文学网站,“弄堂网”上开始写起来的。
“弄堂网”上有读者叫好,要他继续写下去,在与读者的互动中,他有时间就写一段、写一段,最后写成了《繁花》这部长篇小说。
这同样是一个无为而无不为的例子。
换种方法说,《繁花》不是一本循规蹈矩的小说。
开篇的几句,“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
《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骑马觅马,英雄暗老,电灯下面数钞票,数清一沓,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拿出一副扑克牌,捻开细看,再摸出一副。
”文字汪洋恣肆,如天外飞剑,至少我写不出来。
“弄堂网”我也上过,还有“小众菜园”,落花流水春去也,可惜这些网站都不在了。
我也喜欢《繁花》中“夜东京”饭店的呈现,令人印象深刻,洋溢着上海这座城市特有的感性与韵味。
“夜东京”,螺蛳壳里做道场,菜色精美,老板娘铃子风情万种,若拒还迎。
“夜东京”虽小,却自有一番温馨烟火气,更有上海老房子狭隘的空间所挤出的密切邻居关系。
红尘食欲情欲,相得益彰,在烛光摇曳中,旖旎多姿,这些是导演王家卫最擅长的镜头画面,处理得游刃有余,回肠荡气。
玲子有她贪婪的一面,却又有上海女人的精明和决绝,用《繁花》中的话来说,该“拗断”就“拗断”。
在电视剧的结尾,她已准备把“夜东京”连锁店开到香港去。
差不多比“夜东京”稍早几年,我与朋友俞光明经常去一家名叫“家小”的个体户小面馆,颇有“夜东京”风味,就在上海工人文化宫旁的一条小弄堂里。
店面是从石库门前厢房搭出来的,一共就两张半桌子。
生意好的时候,要与公用厨房的邻居借炉灶。
酒香不怕巷子深,个体户的小面馆比国营店家更会做生意。
“家小”的特色是老母鸡汤煨面,热炒过桥浇头,老顾客可以用浇头下酒。
老板娘也会时不时推荐,今天的大黄鱼特别新鲜,明天的葱油鸡产地好。
卞之琳先生来上海,她的推荐是双明虾过桥。
卞先生十分满意,还在签到簿留下了几句像诗的话。
大意是说这样的服务、美食在一般的国营店家无法想象。
“家小”面馆的老板娘不懂诗,可惜了,风情也不如玲子。
倒是有一位叫燕子的女服务员,有点像玲子,更年轻,也稍丰腴些。
卞先生的弟子、我的同门师兄高庆琪,来上海组稿,我也带他去过“家小”。
高师兄对燕子相当倾倒,真写了几行浪漫主义激情的诗,宾主尽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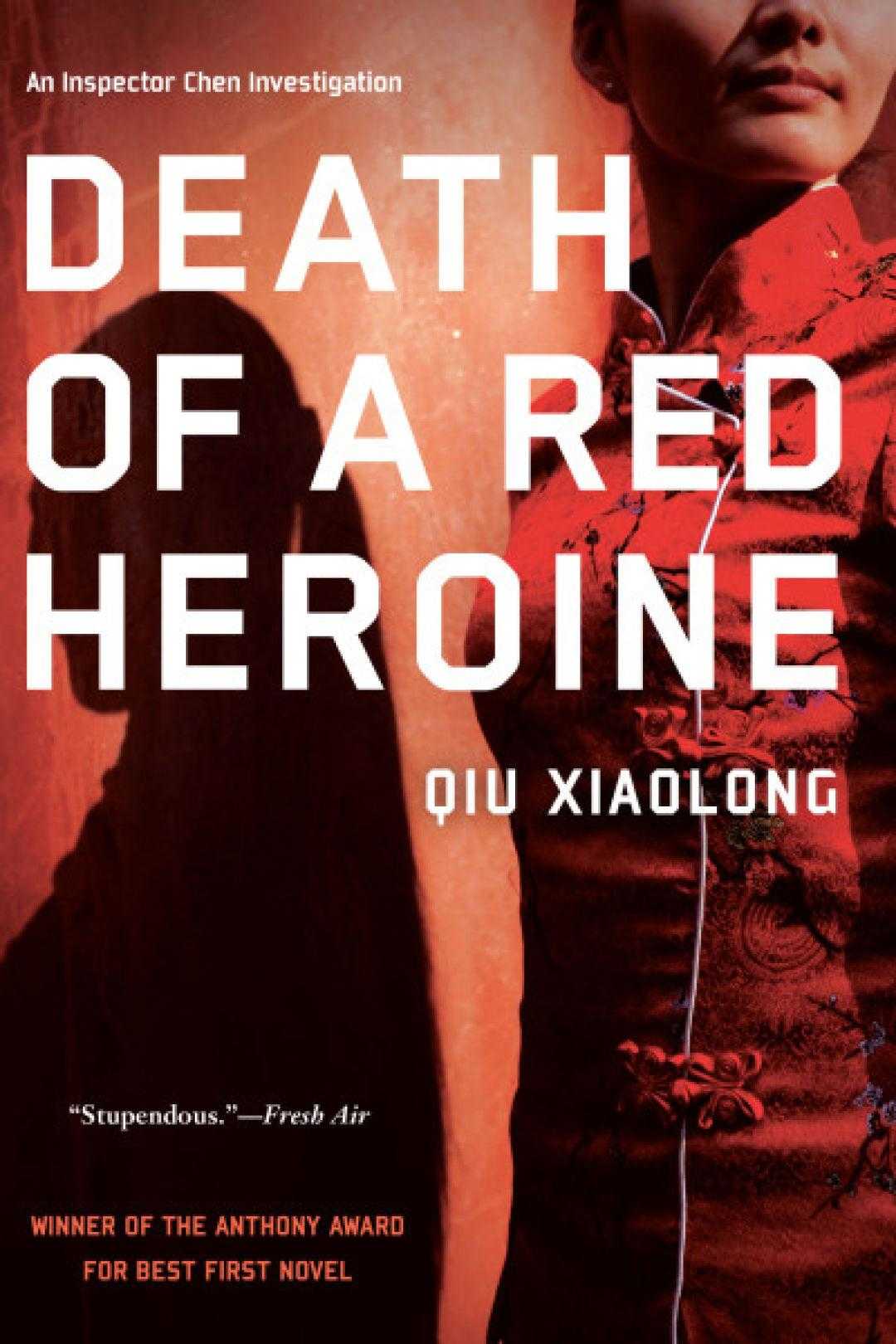
本文
维特根斯坦有段名言,“我语言的局限意味着我世界的局限”。
金宇澄在小说中对上海方言的实验性应用,拓展了现代中文语言世界的地平线。
这在沪语版电视剧中,同样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记得电视剧字幕中出现过上海话“摸子”一词,还在一旁加了注。
确实,有些上海话有着普通话所不能包涵的意蕴和丰富性。
又如上面关于小毛三兄弟那段引文中的“拗断”,就要比普通话中的“决裂”,“断交”生动,声音上也更传神。
或许,能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听到互文性回响。
如周邦彦诗中“秋藕绝来无续处”,也就是“秋藕拗断了,再也无法接起来”的意思。
在小说《繁花》的结尾,有点像《红楼梦》中繁花落尽,只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的悲悯。
电视剧《繁花》结尾,花事却依然一片火红,阿宝仍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就这一点而言,我更喜欢小说。
当然我也完全理解今天的电视剧。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句名言,“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
他的意思是,历史的书写其实都与对当代的种种延伸开去,历史的阅读,也同样与对当代的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解读,一部作品的产生还涉及各种话语的抗争、谈判、妥协等因素。
于是,我们还要回到金宇澄的那句名言:不响。
(原题“不同话语体系中的《繁花》”,现标题与小标题均为编者所拟)
裘小龙
责编 刘小磊
复制本文链接攻略资讯文章为拓城游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